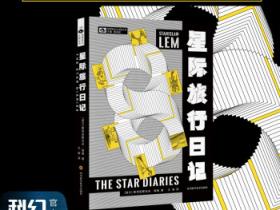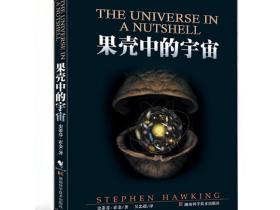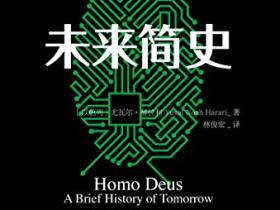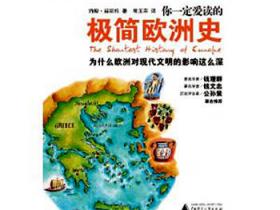《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作者是尤瓦尔·赫拉利,于1976年出生,是全球出门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作者的研究领域是世界历史和宏观历史进程,对大众出版领域与学术研究都有浓厚的兴趣。《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是以色列畅销书,同时,该书也让作者出名。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分为四大部分: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的融合统一和科学革命。通过这4大部分描述人类大历史。一大开创性在于打通文字发明前后历史的界限;填补传统人类史的3大鸿沟:历史观与哲学观之间的鸿沟(提供有史实根据的深刻哲学思考)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的鸿沟(读者多从生态来思考,而不是只讲人类的利益)集体和个人之间的鸿沟(检视历史事件如何影响到当时一般人的生活)。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告诉我们人类是怎样在地球上生存的,农业以及科学存在的时间是如此之短以至于我们不应该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用通俗的语言和新鲜的视角,将个体的幸福放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审视,不再错过历史中关键、有意思的部分。 涵盖了生物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一书,文学,伦理学等众多领域。也涉及幸福, 生命的意义等众多话题,有人说这是一部个人幸福探索之路。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吸引力主要来自作者才思的旷达敏捷,还有译者文笔的生动晓畅,而书中屡屡提及中国的相关史实,也能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好像自己也被融入其中,读来欲罢不能。
序言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毅
前不久听说,业内最近出了一本“奇书”,英文书名叫做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Mankind,中文书名译作《人类简史》,作者是个名叫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以色列年轻人,书在2012年以希伯来文出版,然后很快就被翻译成近30种文字,不仅为全球学术界所瞩目,而且引起了一般公众的广泛兴趣。一部世界史新著竟能“火”成这样,实在是前所未闻。所以,当中信出版社为求一个中文版序而给我发来该书的英文版和中文译稿时,我也就出于好奇而暂时应承了下来:先看看吧。
而这一看,我也就立刻“着道”了——拿起了就放不下,几乎一口气读完。吸引力主要来自作者才思的旷达敏捷,还有译者文笔的生动晓畅,而书中屡屡提及中国的相关史实,也能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好像自己也被融入其中,读来欲罢不能。后来看了策划编辑舒婷的特别说明,才知道该书中译本所参照的英文版,原来是作者特地为中国读者“量身定做”的,而且他给各国的版本也都下过同样的功夫——作者的功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赫拉利也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青年才俊。他1976年出生,2002年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获博士学位,曾专攻中世纪史和军事史,发表过《骑士时代的特殊战役(1100-1550)》(2007)、《最后经历:战场启示和现代战争文化的创生(1450-2000)》(2008)等专著,以及若干有关战争史的论文。在经历了这些微、中观的历史学专门训练之后,赫拉利便转向了一种极宏观的世界历史研究,而且还特别热衷于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等等学科的角度,对作为一个物种的智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做出全方位的考察和预测。老实说,如此大规模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计划是令人瞠目的,那似乎不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凭一己之力就能够成就的事情。然而,赫拉利还真的就单枪匹马地做了这么件不可能的事,而且事实证明,他做得不赖——我们面前的这部《人类简史》,作为他这一工作的初步成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而赫拉利本
人自然也能因此而暴得大名:毕竟,能够像他这样从容游走于这么多学科之间的历史学家,是旷世罕见的。
当然,这件事还是有些令人生疑。且不论赫拉利在书中对人类学、生态学和生物工程学等“硬科学”的运用是否无可争议(那不是很多不明就里的外行读者立马就能明判的),这位“旷世罕见的天才历史学家”一下子结合那么多“硬科学”,用不到500页的篇幅写出的从石器时代智人演化直到21世纪政治和技术革命的一整部“人类史”,在“专业历史学家”看来,恐怕已经很难说还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了。而且,由于缺乏对构成世界历史进程的许多重大事件或现象的系统叙述和解说,这本书恐怕连“宏观世界史”都算不上。可是,如果不是历史,它又能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写历史写到这个份儿上,一般都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离开了“历史”而走向了“哲学”——而且这“哲学”还不止是“历史哲学”,它同时也涉及很多人生的哲理。因为系统的史事在这里隐而不见,流出笔端的都是一些被用来说明某种历史法则、人生道理的史事片段或现象。如果作者能真心关切人类的命运,并且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和理论修炼,这种写作就能达到一种胜境,它的产物也就不再是那种我们所习见的历史作品,而有可能是一种对历史和人生的彻悟。应该说赫拉利就是怀揣这一“野心”来写他的《人类简史》的,而他的努力看来也没有白费。
读《人类简史》,我们每每会为作者非同寻常的想象力而赞叹。比如,他竟能从用生物学制造的那只背上长耳朵的老鼠联想到32000年前的施泰德“狮人”(读来有些瘆人),并能匪夷所思地产生“弗兰肯斯坦如今正坐在吉尔伽美什肩上企图灭绝智人”这样的奇想。这让他的书多了不少一般史学作品所缺乏的文学感染力。但更值得我们欣赏的,也许还是洋溢于全书的一种对天下众生的“无边大爱”。赫拉利无疑是痛恨“人类中心主义”的。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罪恶的人类中心主义,把具有神一般的能力、本来应该成为宇宙间“正能量”的智人,变成了一种不负责任、贪得无厌又极具破坏力的怪兽,结果给地球生态带来了一场“毁天灭地的人类洪水”。他对人类完全无视家禽家畜的心灵感受、用种种变态的养殖方法获取美味的行为提出的几乎声泪俱下的控诉,显然也不是故作矫情,而纯粹是出于一种大慈大悲。正由于有这样一副关爱弱者的菩萨心肠,赫拉利在说起历史上和现实中只对强者有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消费主义、男性霸权,以及总是在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的科学时,自然也没有好气,基本上都是揶揄和批判。总之,他认为迄今为止的智人历史,大行其道的都是这些乱七八糟、一无是处的东西,因而“历史从无公正”,而所谓的“智人”呢,其实一点也不明智,相反是一个非常糟糕、令人失望的物种。
不过,如果把智人历史整个地斥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显然也有失偏颇。实际上,赫拉利也没有这样做。譬如对于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在向“全球帝国”演进这一发展趋势,他还是相当肯定的,因为他觉得非此不能消弭战争、实现环保和保障人权。当然他也没忘记特别强调了一下,说这种“全球帝国”是一种“不受任何特定国家或族群管辖”的世界政治秩序——这种强调,在“新帝国论”甚嚣尘上的当下,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读者也会看到,尽管对智人的行为有许多不满,赫拉利内心里还是“爱人”的。他对智人的所有批评,说到底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埋怨,而深藏于其中的,其实还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忧虑,以及对智人幡然悔悟、痛改前非的殷切期待。赫拉利对当下基因工程学“改良”人类的种种做法的尖刻抨击,便充分显示了他的这种“爱人”情怀。他把打着“治病救人、延长生命”的旗号改造人类基因的科学活动,恰切地比作追求长生不老的“吉尔伽美什计划”和创造科学怪人的“弗兰肯斯坦博士”这两种传说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在他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因为首先,在当今贫富差距已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这种只有一小撮富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永生大法必然严重加剧社会不公;其次,如果人类真的被升级为另一个物种,实际上是升级为一种“永远年轻的生化人”,那么随之发生的就只能是人类的本质乃至“人”的定义的根本改变,就只能是智人历史的终幕。
人类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自我毁灭,想来令人毛骨悚然。赫拉利自然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他试图做点什么来阻止这种看来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演进,而他所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弱弱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究竟想要什么?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他已经在书的倒数第二章中,通过对“快乐”问题的某种历史哲学式的探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发现,“快乐”这种情绪的历史,是历史学家从来不感兴趣的问题,而那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为一旦人们发现历史能证明乐无常态而知足常乐,发现我们过去对快乐的历史认知可能都是错的,发现对快感的执着追求可能只会适得其反地导致痛苦,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走向对自己的真正理解,也就可能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了。
当然,对于这种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问题,赫拉利的回答离真正的答案可能还很遥远。然而他的努力是可贵的。我相信,读了他的这本书之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一旦那传说中的“人生真谛”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感悟,智人的历史或许就不仅能长久地继续下去,而且还能呈现出更健康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