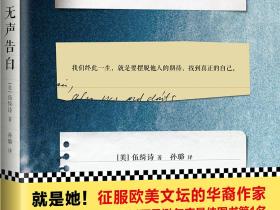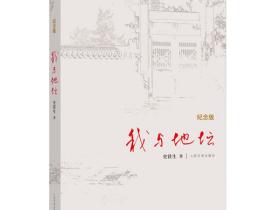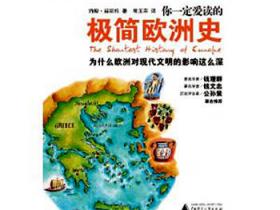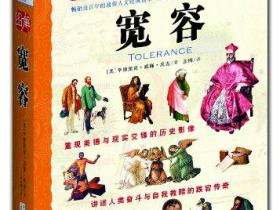天津外国语大学赵彦春教授最新译作《英韵三字经》日前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三词对译三字的《三字经》英译版本。《三字经》以三字之简横贯古今,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包容天地万物之杂,汇聚华夏文化之粹。南宋至今,许多传教士、汉学家将之译为英文,推广海外。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以独特的“三词格”来阐释《三字经》这部中华经典中“三字”这一显著特点,不仅在形式上做到完全吻合原著的特点,兼顾了原著的形式之美,在音节和押韵方面更是做到丝丝入扣,形神兼顾。然而在诸多译本中,从“音”、“形”、“义”三方面来兼顾的译本却很少。《英韵三字经》以英文三词对译汉语三字诠释原著,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使译著同样也适于英语国家的读者朗读记忆。据了解,《英韵三字经》是《三字经》英译的第十三个版本,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将为阐释、解读中国国学经典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学经典《三字经》的海外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赵彦春译《英韵三字经》经文节选:
rén zhī chū
人 之 初,
xìng běn shàn
性 本 善。
xìng xiāng jìn
性 相 近,
xí xiāng yuǎn
习 相 远。
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
gǒu bù jiāo
苟 不 教,
xìng nǎi qiān
性 乃 迁。
Jiāo zhī dào
教 之 道,
guì yǐ zhuān
贵 以 专。
With no education,
There’d be aberration.
To teach well,
You deeply dwell.
xī mèng mǔ
昔 孟 母,
zé lín chù
择 邻 处,
zǐ bù xué
子 不 学,
duàn jī zhù
断 机 杼。
Then Mencius’mother
Chose her neighbor.
At Mencius’sloth,
She cut th’cloth.
dòu yàn shān
窦 燕 山,
yǒu yì fāng
有 义 方,
jiāo wǔ zǐ
教 五 子,
míng jù yáng
名 俱 扬。
Dough by name
Fulfilled his aim.
His five sons
Became famous ones.
yǎng bù jiāo
养 不 教,
fù zhī guò
父 之 过。
jiāo bù yán
教 不 严,
shī zhī duò
师 之 惰。
What’s a father?
A good teacher.
What’s a teacher?
A strict preacher.
zǐ bù xué
子 不 学,
fēi suǒ yí
非 所 宜。
yòu bù xué
幼 不 学,
lǎo hé wéi
老 何 为?
An unschooled child
Will grow wild.
A young loafer,
An old loser!
另外,赵彦春教授还出版了一本《三字经英译集解》,里面详细的阐述了《三字经》的要义,并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英译本进行平行文本分析,一是翟理斯的阐释性散体译本,二是赵彦春教授的三词格偶韵体译本,三为王宝童的诗行词数不定的韵体译本。
具体事例如下: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
此 节经文是《三字经》首篇,它以人性开篇,统领全经。前言中对马礼逊等译本的分析表明,要想译好此节经文并非易事,这不仅仅要求译者具备扎实的语文知识、对 翻译机制的深切透视,还要求其对中西方人性论,乃至本体论、价值论、目的论有所体悟。中国文化中,有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间的论争(参见冯友兰 1985)。 《三字经》为儒家经典,其所依据的自然是亚圣孟子的性善论。姑且不论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类根本性的命题,译文如果不能达到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性这一哲学 高度,势必会贬损《三字经》所蕴含的哲学价值。《三字经》从人性谈人伦和教育等问题,这与西方文化不仅不对立而且还可以融通。西方文化关于人性这一问题, 其实也是“性本善”这一基调。《圣经》上说:And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in theimage of God. He created hi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神 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依据《圣经》,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人,上帝即善,故人亦善。在孟子这里,人性变 异或变坏是后天因素造成的,而根据《圣经》,人性的恶肇始于撒旦的引诱。刨除语言表征上的差异,此两者均说明人性的恶不是本原的。赵译综合自己对中西方文 化的认识,给出了最初的译文:
Man the breed,
Of good seed.
The same nature,
But varied nurture.
第一行译文中的“man”是全称意义的,其同位语“the breed”则凸显人这一物种和《圣经》创世记中反复申明的各从其类(according to its/their kind)——其实,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认识或划分也是各从其类的,《周易•乾》说:“本乎天者亲上,本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而“good seed”则强调初始的、本源的善。“good seed”也源于《圣经》,比如:And he (Jesus)gave them another story, say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like a manwho put good seed in his field. [他(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而且,理雅各(Jacob Izrael)也被称作“亚伯拉罕的子嗣”(Seed of Abraham)。作为物种的“the breed”与作为初始状态的“good seed”相照应,应能充分表现“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
中西文化混则相同,析则相异。所谓相同,即万物本原意义上的同一;所谓相异,即在事物表征上的差异。在西方,人性的恶源于撒旦的引诱——在此意义上本善或 本恶都解释得通,就看人性从何算起了——人性的开端,如果从夏娃堕落算起,则性本恶,即所谓的原罪;如果从上帝造人算起,则性本善。但是,不管怎样,中西 文化有一个共同点,即起初人是善的。
《三字经》与《圣经》虽然一中一西,但是在精神上却并非不可以兼容,因为两者所述都是先善后恶。那么,译者该如何跨越语言的障碍而求得译文的最大等值呢?基于此,译者不能只停留在文字的表面而应该深入到“两种语言习惯的心灵深处”(王宏印 2007:207),在译语中求得两种文化的融通。赵译以天然的“nature”与人工的“nurture”相对举——前者是“性”,后者是“习”;前者是天然,后者是人工;前者是派生万物的道;后者是体现道的德;前者是与生俱来的性;后者是人力所为的伪。由此可见,“nature”与“nurture”不仅具有形体上的相似性而且也押韵合辙,巧妙地表现了“性”与“习”的对立与关联,同时也蕴含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之间的分立与归一。通过译文,西方读者应该能体会“性本善”的真正含义以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乃至可能的互文关系。
但是,赵译还是废弃了这一译文,而代之以进一步深入到文化深层,同时在整体上也更逼近原文的现译文。
在动手英译《三字经》之时,笔者电话邀请延安大学的叶友珍,约定以三词格偶韵体同时英译。她很快便给出前两行的译文:“Man at birth,/Good on earth.”令人眼前一亮,真可谓形神兼备!受此智慧之光的闪击,赵译有了在字面上也逼近原文的想法,于是便做了相应调整:“Man at birth,/Being of worth.”“Man at birth”更接近“人之初”,而且“birth”有物种创生和个体出生的双关意义或联想。人性本一,后天之“习”使之异化。因此,“The same nature”承前,“Varies on nurture”随后,叙述了人性变异的根源。
这里有必要阐明“Man at birth,/Being of worth.”的语法构成。这是小句(small clause)构成的表意单元。“being”的措辞是有斟酌的,它一语双关:一、它是“be”的现在分词,与“ofworth”构成系表结构;二、它是“be”的动名词,即“being”为名词,“of worth”则为定语或附加语。在西方哲学中,“being”即“存在”是最重要的哲学术语,暗涉本质的“essence”。“essence”的拉丁语词根为“esse”,相当于“be”。这样,“essence”与“being”就在哲学意义上连通了。而“worth”也是重要的词项,且看“worth”与“Word”(即“道”)之间的关系:两词同源,因此具有源于道、本乎善之意。
以下且援引Guoëffic(1996)对“word”与相关词或派生词的词源考察(参见赵彦春 2004:47),以说明“Word”或“道”的文化内涵:英语的word (“道”)本义为“男性生殖器”,该词以“v+元音+r”(“vVr”)为原型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词汇家族,而“vVr” 源于verpa L., verge, Fr., penis, 及 vir, man。
Guoëffic的研究表明:道,即生,即善,即德,即工,与中国的“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道、生、善、德、工之类以及西方的“Word”与中国的“道”不过就是同一本原的不同表征。
不过,斟酌之后,觉得“Man at birth,/Being of worth.”不够通俗,语体上与原文有所出入,故而改为“Man on earth,/Good at birth.”
赵译此节译文几易其稿,旨在保守形意张力和意义潜势的同时也兼顾中西方文化尤其是中西方哲学的异同和内涵,以期打破中西哲学、文化和诗学的蔽障,架起异域天堑的通途,真正达到“译,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的根本目的。
西方译家筚路蓝缕,多有建树,对传播中华文明也可谓厥功甚伟。然而,由于其文史哲纵深不足以及翻译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他们难免望文生义或者泥古不化,同时 又不能兼顾原文的诗体特征,因此其译本多有舛误和缺失。我辈虽有感恩之心,却难能苟同了。我们应当记取的是: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文辞对应,而应深入到中西文 化之源,而后根据诗体特征,瞻前顾后,左右逢源而达至译文的圆满调和。
关于译诗,西方学者也早有以诗译诗的论断。邓哈姆(Sir John Denham)有言:诗歌翻译不是语言对语言的翻译,而是诗歌对诗歌的翻译(not Language into Language, but Poesie intoPoesie)。(参见Bassnett 1980: 59) 然而,翟理斯及西方译家似乎只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翻译或阐释,其结果自然没有表现出诗的特质或本性。本土译家中有人试图“再现”《三字经》的诗体形式,精神 可嘉,但是其效果未必理想,其缺点在于重形式而废内容,主要体现于因韵害义。我们必须强调,形式是与内容密不可分的而不是外在于内容的虚设。诗歌的形式, 并非只是一种花瓶式的摆设,而是因其极大地有助于诗情诗理的表达而构成诗歌内容的一部分。(张智中 2008:109)在诗歌中,形式与内容成了彼此依赖、须臾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诗性的根本所在。基于此,就韵诗翻译而言,不当的韵与无韵都是对译文的减损。
翟理斯译文为无韵的散体,在体裁上与原作这一韵文已不对等,自然是不充分的译作,而其全力阐释的语义实际上也并不准确。前言中,笔者已对翟理斯此节译文进行了分析,此不重复。现在,且让我们翻开王宝童先生的韵体译本,以对比、赏析:
At first mankind
Is kind at heart,
With natures alike
But habits apart.
(王宝童)
乍一看,王宝童译本与原文异曲同工,几近形神兼备,只可惜,这只是与原文相对应的措辞以及诗体形式给人的错觉。实际上,它没能再现原文之旨,而且其笔法也不够纯熟。此译文与《三字经》这部经典差距甚大。
纽马克(Newmark 1979:101)就翻译批评曾有过如此论断:“译作的妙处正如诗的妙处一样,不可言传……但翻译中的败笔、错误和不确却不难发现。”以下,我们且对王译进行考察,看看有何妙处抑或不足。
在形式上,王宝童译本尽管整齐,但是它与《三字经》没有可资类比的关系。具体说来,此节译文虽然很工整,但并不是其书名“The Triword Primer” 所标明的三词格,因为此译第二行便不是三个单词。如果从音步上看,王译也没有可以与《三字经》相类比的形式关系,因为它没有设定明确的、对应原文韵律的音 步。通观王先生整部《三字经》译文,其诗行从两个单词到六个单词不等,失却了《三字经》的标志性特征,换言之,其译文与其书名即“The Triword Primer” 名实不符。形式上与《三字经》无关联,那么内容又如何呢?其实,如前所言,形式与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了诸如此类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诸如此类的 内容。不过,我们还是启用低限度的要求,定点考查其语义的传达。如果语义的传达不到位,也势必丧失原作的精神。在翻译的转换过程中,如果原文的精神被蒸发 掉了而又没有得到新精神的补充,那么这样的译文便成了邓哈姆所说的“残渣废物”(Caput mortuum)(参见Bassnett 1980:59)。就此,我们也看看此节译文是否再现了原文的精神。
第一行译文忠实于原文的“人之初”,而且用词准确,但是从第二行起便可发现诸多不妥之处。首先,“at heart”便有画蛇添足之嫌——“kind”可以释义为“tender-hearted”,也就是说,“heart”作为语义因子已被编码于“kind”之中了。不仅如此,“kind at heart”还会引发外表上不和善的联想,即外表不善只是心善。其次,第三行的“性相近”译为“With natures alike”在文辞上似乎很接近原文,其实却不合情理。人性为一,而“natures”为复数,据此译文,人性既为“一”又为“多”,便违背了排中律,致使“一”与“多”相抵牾。以此可见,复数形式的“natures”不适于表征人性这一全称意义,而且它与全称概念的“mankind”连用也属不当。再次,第四行的“habits apart”在字面上看似对应原文,但是在语义方面却相差甚远,可以解读为“习惯分开”“分开的习惯”,等等。这一措辞不仅偏离原文所述之“习”——“习”大致相当于英语的“nurture”“performance”之类,而且行文本身也嫌怪异,即读者很难明白“habits”为何是“apart”的,其与“性本善”又是什么关系。更严重的是,王译完全背离了此节经文的主题。本节经文叙述的是人性由善转恶,而王译表明人性并没有变恶,只不过是“habits apart”而已。王译此病不难诊断:一是没有明白“习相远”是何意义。“习”是“性”变异即“相远”的原因,而非王译所表明的那样“人是善的,本性相同而习惯相异”,二是迁就“apart”与“heart” 押韵之故,为凑韵之弊。王译专注于韵而忽略了本节经文的主题和文脉,以致完全违背了原文之旨。在许多译家那里,韵成了译诗必不可少的要件,然而与原文内容 相比,这样的韵往往只是与内容毫无关联的虚设。不过,此韵并没成为虚设,因为它损伤了诗的内容,蒸发了原文的精神,使之成了邓哈姆所说“Caput mortuum”。
本节经文统领《三字经》全文。正因为人性的“习相远”才有了教育的必要,而这正是《三字经》得以成书的因由。然而,王译竟然遮蔽了这一重要内容,致使其所谓的“The Triword Primer”失去了统领性的话语。
综上分析,此节译文朗朗上口,然而与原文却是貌合神离。语义冗余和悖谬以及凑韵之弊使它丧失了预期中的价值,唯其如此,也便失却了原文的精神和不可言传的妙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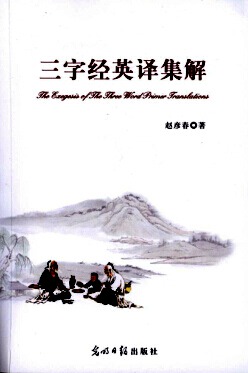
天津外国语大学赵彦春教授最新译作《英韵三字经》